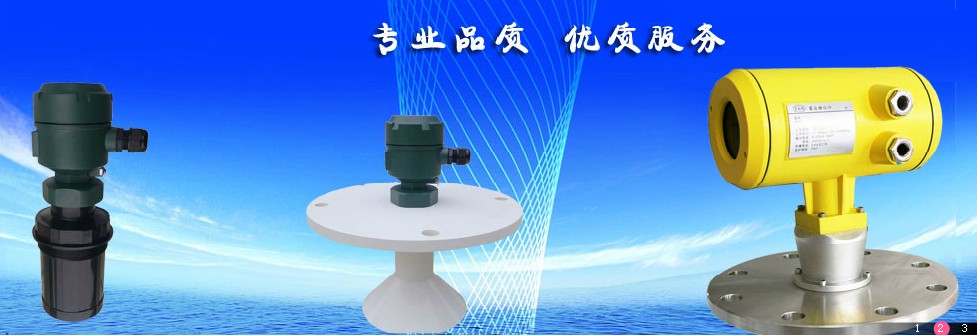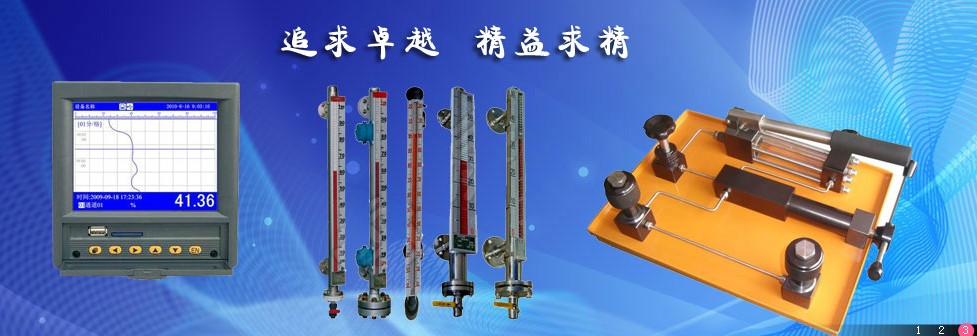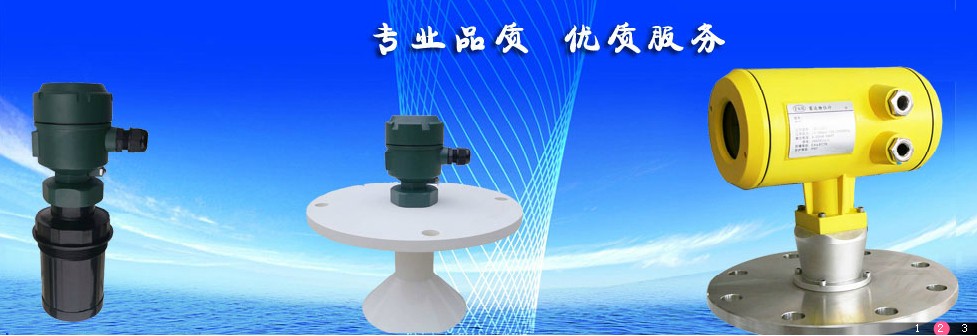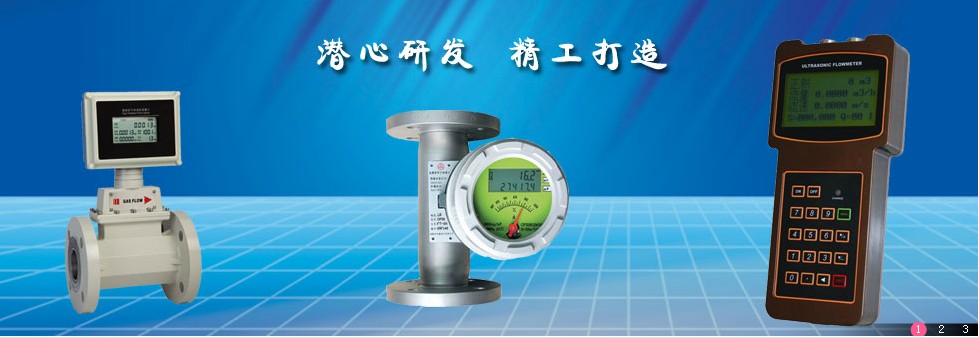网络众筹,法律监管失治成“众愁”
点击次数:2019-11-21 08:48:27【打印】【关闭】
近年来,轻松筹、水滴筹、爱心筹等平台蓬勃发展,成为个人大病求助的重要渠道,推动了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然而,在慈善平台上,一些诸如诈捐、善款挪为他用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这让“行善者”多了几分犹豫与不决。
就在本月初,一起司法案件回应了公众的期待——让善款回归善心人: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定,筹款人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情况,将筹集善款挪为他用,构成违约,判令筹款人全额返还筹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据悉,这是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救助纠纷在司法上作出的判决。
挪用筹款应否返还?
出生三个月后,莫某的儿子被查出患有威斯科特-奥尔德里奇综合症,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治疗时,医生提出要进行心脏移植治疗,这笔费用大概要四五十万元。为此,2018年4月15日,莫某在水滴筹平台上,以“无醇的五粮液”为名,发起目标为40万元的筹款:“孩子患病5个月来饱受折磨,目前已花光家里的全部积蓄,欠下了20多万元的外债。医生说后续至少要40万元左右的治疗费用,我和妻子的工资不足以支付孩子的治疗费用……”
几天时间,莫某筹得153136元。4月18日,水滴筹将所筹款项支付给莫某。
2018年7月23日,莫某的儿子因病去世。与此同时,水滴筹平台收到举报,称莫某并未将款项全部用于儿子的治疗,同时存在隐瞒家庭财产的情况——莫某名下不仅有车,其父亲的门面店,每年可以收租金6万元。
水滴筹方代理律师称,调查发现,莫某获得的筹款,其中10万元用于偿还债务。根据《水滴筹个人求助信息发布条款》规定,当受助者因疾病或其他原因去世时,筹款项目发起人应当立即通知平台,退还筹得款项。如果发生隐瞒真实情况或发起人获得筹款项目后放弃治疗,或存在挪用、盗用、骗用等行为时,平台有权要求发起人退还全部筹得款项。
莫某在庭审中承认,确实将所筹款项中的10万元,偿还给了他的姑父。
“但之前借钱,就是为了救孩子,给孩子治病,也相当于钱用于患者治疗,剩余筹集款项中的3万余元也用于后续治疗。”莫某不认可自己存在隐瞒家庭财产的情况:“水滴筹工作人员未明确对患者祖父母的财产情况也进行审核,家里出租的店面归孩子祖父母所有,患者的医疗费应该由其监护人来承担。”
法院判决指出,求助人是否应该返还赠与人筹集款项,应从求助项目真实性和是否违反合同约定两方面审查。根据水滴筹平台上要求的承诺、《水滴筹个人求助信息发布条款》规定,公布经济收入的范围不涉及患者祖父母。然而,莫某隐瞒名下有车,也没有说明其获得爱佑慈善基金会、上海市未成年人罕见病防治基金会救助的情况,违反了规定。“莫某确实为孩子治疗举债,且筹集款项也确实用于偿还因之前治病而欠下的债务,但与本案中双方原本约定的患者治疗时间、用途不一致,属于违反合同约定。”
据此,法院判决莫某全额返还筹款15315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记者获悉,11月18日,莫某已主动退回全部筹款和利息。同时,水滴筹平台称将在5至7天内全部退还给赠与人。
筹款平台有哪些权利义务?
案件虽已落幕,但涉及互联网个人大病众筹行业的问题探讨却没有停止。对于个人网络众筹的定性问题,也引发业内思考:个人求助受不受慈善法的调整?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个人求助,求助人和筹款平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个人并没有发起募捐的权利,只有被授权的慈善组织才可以募捐。将个人求助与募捐区分开来,是立法设计保留的个人权利,在遭遇困境时,个人可以向社会发出求助。”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说,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个空间的存在,成立了大量以此为业的平台。
对于平台、发起人、赠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慈善联合会法律顾问张凌霄认为,平台和其他两方都构成了合同关系。“平台和赠与人之间成立委托管理的合同关系,对赠与人的资金进行监管;平台与发起人之间也形成合同关系,平台确定发起人发布的信息为真后,把钱支付给发起人。”张凌霄解释称,个人大病筹款平台虽然不向求助者收取费用,但是平台负有严格的审核义务,应该对发起人的信息真实性、善款的使用担负起审查责任。
记者注意到,在莫某案件中,主审法官在判决书中特意提到,水滴公司并非慈善组织,也不是民政部门指定的公开募捐平台,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更应在运营水滴筹平台获得合理利润的同时,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审核机制,配备与求助规模相适应的审核和监督力量。“然而,筹款平台在审查方面存在瑕疵,没有尽到严格审查的义务,在随后的善款使用方面,也没有尽到监督义务。这虽然不影响法院的最终判决,但是在对赠与者的善款保护上并未尽责。”判决指出。
平台存在审查瑕疵会令赠与者的钱财用途改变,平台若以居间方为由逃避责任,也是众多法律界学者强烈谴责的行为。在筹款平台与众多赠与人通过《用户协议》达成的合同中,通常平台都会称自己仅为发起人与赠与人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渠道,不对项目做任何形式的担保,对于因项目发生的一切纠纷,由发起人、求助人和赠与人自行解决。“这显然是刻意减轻自身义务的条款。”专家表示。
正是因为这些条款的存在,在发生纠纷时,有筹款发起人质疑:平台是否有权代表众多赠与人追回筹款?记者注意到,在莫某案件中,法院指出,赠与人与水滴筹平台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也包含《水滴筹个人求助信息发布条款》,条款要求在发现发起人挪用、盗用、骗用等行为,水滴筹平台有权要求发起人返还筹集款项的规定。
同时法院考虑到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中赠与“小易快多”的特点(即数额较小、支付容易、筹集迅速、赠与人多)、大众对于水滴筹平台的通常理解、水滴公司自身认知等因素,认定在约定的特殊情形下,赠与人可以授权平台代表赠与人要求莫某返还筹集款项。
善款被挪用、平台审核不到位,与法律规范的不健全不无关系。记者注意到,2016年实施的慈善法对个人求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后来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如《江苏省慈善条例》《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也仅规定,个人求助要对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虚构事实、夸大困难骗取他人捐赠,没有明确求助人应公布求助信息的范围。在平台方面,也没有规定判定求助信息准确性、全面性、及时性的审查标准,以及违反该义务的法律责任承担。
谁来监管筹款平台?
对于筹款平台应该归谁监管,也是法学界关心的问题。
在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国科看来,民政部门来管理个人网络求助行业可能更为合适。“从社会功能上讲,普通民众并不知晓,在水滴筹等平台上的筹款属于个人求助,而非募捐。”何国科说,个人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求助信捐钱,不会认为是个人求助,而是觉得自己在做公益、做慈善。也因此,个人求助中诈捐、挪用善款的问题频发后,影响的会是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政部门应该发挥监管的兜底作用。”
金锦萍则认为,民政部主管的机构都是非营利性质的。虽然说网络筹款平台业务跟民政部急难救助、扶贫有一定关联,但并非纯公益性质。作为营利的企业,平台提供渠道,让个人进行大病求助,这种行为更应该像企业一样归工商部门管理。“企业从事这项业务,首先要在工商部门登记该业务范围。如果没有这个业务范围,工商部门就要采取措施。如果有这个业务范围,就可以看做企业行使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法律是不会阻止企业行善的。”
“目前按照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民政部门去监管网络众筹平台,这也不是民政一个部门可以办成的事情。”在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调研员李莉看来,构建一个由民政、工商、网信、银保监会等部门主导的联合监管机制,对互联网个人求助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水滴筹等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发布的求助信息获得了超过2亿爱心人士的响应,筹款超过220亿元,救助人数超过280万人次。越来越多的个人通过这种救助方式受益。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完善相关措施,让这条救助之路更加合法合规?
在莫某案件判决后,朝阳法院从多个层面提出了建议。
就求助人而言,应要求其提供的信息真实、全面,明确求助人负有全面履行附义务赠与合同的义务及违约责任。如果求助人未履行约定义务将善款用于“治病”,应承担返还筹集款等违约责任。
网络求助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对发起求助、善款筹集、使用追踪的全过程履行严格形式审查义务和监督义务。在求助人骗捐、严重违约等情形下,网络求助平台经授权还可代表赠与人向求助人主张返还筹集款。网络求助平台应公开、及时、准确地将已返还的筹集款、利息等退还全体赠与人,否则应对赠与人承担违约责任。
作为爱心捐赠一方,赠与人对求助人、网络平台款项筹集、款项使用及返还等情况均享有知情权,赠与人可依据与求助人之间形成的赠与合同关系、与互联网平台之间形成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享有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
在行业自律层面,2018年10月,轻松筹、爱心筹、水滴筹三家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建立了《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启动了行业自律管理。在此基础上,行业应建立专门的自律组织,通过构建风险管理制度、定期通报制度、募集资金第三方托管监督制度,推进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有资金与网络筹集资金分账管理,定期公示,共同维护个人大病求助领域的规范秩序,推动个人大病求助机制良性运转。
平台自律组织也应鼓励各平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优化求助救助的载体和形式,在赠与人个人信息保护、求助人获捐效率提升以及捐助资金安全保障方面有所作为。
在立法完善、平台自律的情况下,监管层面更不能缺位。法院建议将个人大病求助纳入行政监管范围,建立与社保、慈善基金会等相关部门、组织的信息互通共享机制,避免多头捐助、重复施救。